2024年11月3日,《中國青年報報》刊發文章《通識課“理解中國”為何讓大學生直呼“解渴”》,文中引述我院黨委書記何畏關于思政課教學的思考與實踐。現将全文轉發如下:

多年來站在思政課的講台上,伟德bevictor中文版教授何畏收到過不少學生抛來的疑問,有的問題尖銳且敏感。
一名作家曾說“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隻在乎小民尊嚴”。在辨析這一觀點時,有學生提出:“當前已經全球化了,我們是‘世界公民’,再讨論這個問題時是否存在狹隘的民族主義?”
“思政課的教學和科研,一定要聚焦學生的真問題、回應學生的真困惑。”那時,何畏認為,隻有從學理上将問題剖析清楚,在深層次上以理服人,才能從思想根源上真正解決學生的疑問。她當即定下了一項研究課題——《當代世界中的國家與個人——也談“大國崛起”與“小民尊嚴”》。後來,她的這一研究成果又被帶到了講台上,用一堂主題講座“何以為家”回答了學生的提問。
“這種論調把個人的幸福、尊嚴與國家的強盛全然割裂開來,借口‘小民尊嚴’宣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制造民衆與國家的對立。這類建立在抽象人權基礎上的言論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如果不加以反思批判,将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造成持久沖擊。”對此,她在課上以電影《何以為家》為導入分析,深刻剖析當代世界中個人與國家、小我與大我的關系,以及更深層次的國家的起源、政黨與國家的關系。
這堂課的讨論非常熱烈,何畏笑稱,“甚至持續到報告廳熄燈關門,學生還和我一路走一路交流”。
課上課下,類似的來自學生們的思想困惑并不少,何畏都一一記下來,同樣将這些問題轉化為科研課題,又将科研成果回歸到了課堂講授。很多同學向她反饋,“這些回答直面問題,非常‘解渴’”。
在她看來,“隻有回答了學生最深層、最真實、最急迫的思想困惑,他們才能夠‘解渴’。我們需要給學生一把鑰匙,他們可以自己‘開門’,以不變應萬變,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解決問題”。
于是,何畏萌生了一個想法:開設一門新的通識課“理解中國”。
她告訴記者,“過去的這類課程大多以闡釋為主,這門課則是在批判謬誤中闡釋,在對比中回答問題,從而做到在提升社會思潮辨識力中固本培元。隻有幫助同學們去建構理性看待社會的視野,才能夠讓他們真正地理解中國、認同中國,從而熱愛自己的祖國”。
就這樣,何畏帶着一支90後青年思政團隊在2019年年初正式推出了這門新課,在科學回答“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的同時,直面新自由主義、曆史虛無主義等社會思潮和錯誤觀點。課程剛一開啟選課,便被學生“一搶而空”,這樣的“搶手”現象持續了5年。
随着青年學生的思想變化和社會思潮的變化,這門課的教學内容也在不斷變化。“如近幾年讨論較多的泛娛樂主義,還有一些尚未形成專題讨論,但在學生群體中備受關注的‘佛系’‘躺平’‘内卷’‘淡淡的青年’‘平靜的瘋感’等亞文化現象,也被更新進課程裡,并對學生進行答疑解惑、對話交流。”何畏将這些苗頭性現象歸納為“微思潮”。
教學内容在更新,一屆屆學生們的新問題也在不斷抛出。
學生們對“中國式現代化”專題的課程内容非常感興趣,但也會有疑惑,為什麼說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本質區别是什麼?中國式現代化何以代表人類文明新形态?在何畏看來,這些問題都應該在課上作出深刻有力的回應。
“在學術上梳理清楚這些問題,然後将其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教學話語,向學生們把道理講述清楚。”何畏談道,“淺表的灌輸很容易被解構,一旦遇到新的問題,思想還是會産生新的困惑。如果學生樹立了正确的立場、觀點、方法,那自己就可以剖析解決問題了。”
她舉例說,在批判曆史虛無主義時,一方面要揭示其政治意圖,另一方面,還要着重從方法論層面揭露其錯誤根源,以達到對馬克思主義深層次的政治認同和思想認同。“比如抹黑英雄,網上有錯誤觀點認為從生理學角度看,邱少雲不可能忍受烈火焚燒;從力學角度看,黃繼光不可能承受住機槍的沖擊力。問題在一些人的推己及人心态,即‘因為我無法完成,所以他也無法完成,這件事情就是虛假的’。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粗暴的邏輯,其中涉及更深層次的認識就是應該如何看待英雄。”
何畏會告訴學生,馬克思主義認為,偉大與平凡是統一的,英雄人物作為血肉之軀,同樣具有平凡的一面,如果隻見平凡而不見偉大、誇大平凡而否定偉大,就會“推己及人”不承認英雄,相反,如果隻見曆史人物的偉大而神化英雄,就會陷入曆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這是唯心史觀在曆史觀和英雄問題認識上的兩個極端。對此,她覺得,隻有幫助學生從思想根源上将這些問題破解清楚,以後遇到類似的問題他們才能自己進行辨析,“這是學生需要自己掌握的‘鑰匙’”。
與此同時,何畏團隊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持續不斷地提升課程建設質量?
“作為國防背景的理工科學校,我們希望邀請理工類教師加入教學。”她舉例說,講到“創新中國”主題時,邀請了學校雷達領域和智能汽車導航領域研究的80後工科“大牛”共同對話,“我從哲學社會科學角度理解創新,他們從自己的研究領域進行探讨”。
在何畏看來,“通過解讀和對話,與學生互動,才可以讓他們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識,與學生們碰撞出許多不同的火花”。如今,這門課從最初何畏一人主講大多數專題,逐漸轉為團隊成員配合完成。“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講授的專題,也可以兩三個人配合完成,我來補位。”她笑稱。除了主講老師外,每次課教學團隊的其他老師也會參加,共同從各自擅長的領域出發給學生答疑。這個“答學生問”的課堂環節也是學生口中“最期待的時刻”。
讓學生李青青感觸極深的是“泛娛樂主義以及當代青年價值觀”的專題講述。“可能是被幽默、诙諧的表情包,無厘頭、搞怪的段子吸引,這節課我特别專注,這個主題的内容也給了我‘當頭一棒’。”
李青青說:“泛娛樂主義如風一般看不見、摸不着,卻無時無刻不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影響着我們的一舉一動。它以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為載體,夾雜着淺顯、庸俗、毫無文化内涵的形式内容,在給人輕松的感受的同時,也誤導着人們在‘娛樂至死’的路上越走越遠。”這不禁讓她想到,平時在不同的娛樂類App裡浏覽明星八卦時,在随意跟風搶購時,“可能也被流量和經濟效益帶着跑了”。
自從旁聽過一次“理解中國”的課後,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趙書平也被課程“圈粉”了,每年開課,他一有時間就會出現在教室認真聽講。
“‘理解中國’的課程十分與時俱進。”趙書平說。
盡管已經從伟德bevictor中文版畢業,進入複旦大學繼續深造,郭小凡也會在回到南京後,再去“蹭”一節“理解中國”課。他告訴記者,由于學習政治學專業,他對集體與個體的關系、國家與國民的問題特别感興趣,“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何老師從國家學說的角度進行了對困惑的澄清和全新的知識建構,這些内容對我的啟發非常大,甚至影響到了自己現在從事的研究工作”。
今年1月,郭小凡再次坐在教室裡聽了一堂關于抵禦曆史虛無主義的專題課程。“何老師舉例了一部電影,電影中将曆史細節碎片化後重新剪輯,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曆史的主流。”
他看到,許多學生露出了驚訝的表情,“對于同學們而言,觀看這些電影時的第一反應或許是某個演員出演了什麼角色,對于電影人物本身和演員更動情。在這種情感沖擊下,大家很容易忽視電影傳遞出來的價值論調以及隐藏的曆史虛無主義問題。實際上,影視作品也傳遞出了許多需要我們辨析的價值觀念,我們不能僅關注表面内容或角色,還需要回到當時的曆史背景,從不同角度理解它的叙事和結構等問題,特别是要堅持正确黨史觀,牢固樹立唯物史觀,否則對曆史的認識就可能南轅北轍、走向誤區”。
“理解中國”的課程在學生中備受歡迎,何畏團隊編撰的教材《理解中國》也于去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何畏看來,思政課需要通過紮實的理論研究來推動教學,沒有透徹理論研究的思政課無法征服學生。“00後學生檢索資料、獲取信息的能力很強,雖然有時我們掌握的信息量不如學生,但我們的長處是理論基礎和認識水平,通過學術研究将問題掰開了揉碎了再進行講解,道理講透了,才能從思想上赢得學生。”
“同時,思政課必須回答學生的問題,破解和解決其困惑。”何畏認為,對于這些困惑,必須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進行更深層次的辨析,從根源上破解,而不是僅談論現象。在她看來,要在辨析錯誤社會思潮中引領青年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在新一輪課程備課階段,何畏和團隊計劃将“中國式現代化”等内容繼續融入教學,進行更深層次的剖析,為學生樹立自信。“例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一迷思從何而來?我們需要把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講清楚,學生們理解了過去的迷思如何形成,今天我們又如何通過中國式現代化破除迷思,才能在深層次上真正‘解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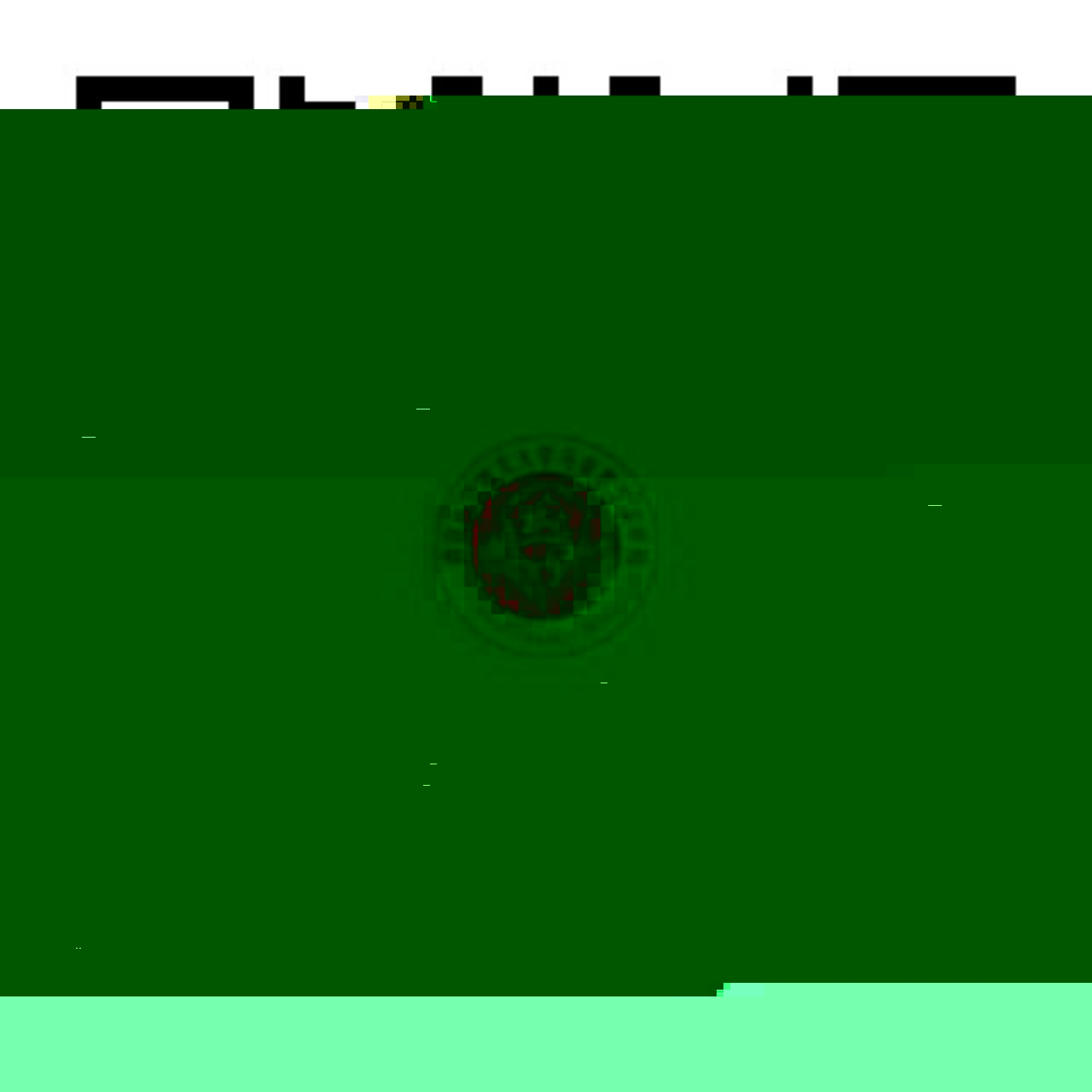
歡迎關注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