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之年。中國在這場特殊的戰“疫”中再一次彰顯出強大的制度優勢和民族精神,國際輿論也從最初的心存疑慮、褒貶不一轉變為普遍贊譽。然而,嚴峻的現實并不容許我們有絲毫的懈怠,國内疫情尚未解除,世界上又有多個國家先後出現病毒蔓延。毫無疑問,對這場疫情的深層反思刻不容緩,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理應肩負起這個責任。
雖然關于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進化和作用機制仍在探索中,但已有的醫學研究均表明,這次疫情的暴發與2003年的SARS存在驚人的相似,即都與非法獵捕和食用野生動物有關。這就提醒我們,人類必須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
1962年,一本由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撰寫的著作《寂靜的春天》橫空出世,猶如一聲驚雷,響徹當時還陶醉于工業文明對自然瘋狂征服的世界,引發了極大争議。身患癌症晚期的卡遜女士因此遭到美國利益相關部門的猛烈抨擊甚至诋毀,兩年後黯然離世。這本經典著作成為生态批判的裡程碑式起點,在一定意義上促成了後來的一系列生态立法和環境保護部門的成立,激勵着一代代環保主義者前赴後繼。在随後的半個多世紀裡,不同領域的中外學者從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等方面對生态問題進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讨。它們以其對自然和生命的熱愛敬畏、對美麗家園的真摯關懷、對生态失衡的愁緒憂患、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性反思,發出“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公地的悲劇”(哈丁)、“自然的反抗”(霍克海默)等铮铮警告,提出“占有還是生存”(弗洛姆)、“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科威爾)等鞭辟入裡的拷問,極大推動了生态問題的理論和實踐發展。
生态系統是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間内,生物與環境構成的統一整體。在這個統一整體中,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并在一定時期内處于相對穩定的動态平衡狀态,因而生物與環境是不可侵害的整體。中國古代就有“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的生态哲學思想,曆朝曆代都不乏環境保護的嚴苛律令。周文王時期頒布的《伐崇令》中記載,如果有人違反禁止填井、伐樹等禁令,一律處死,且不允許赦免。《秦簡·田律》中規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這些都反映了古人對自然的敬畏與保護。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國先後頒布了一系列生态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面對現代社會日益嚴重的生态破壞,黨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布局,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國家目标。黨的十九大再次強調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報告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隻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生态問題,是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産之後的現代生态危機。從根本上來說,它是由片面追求利潤的經濟發展模式導緻的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生态失衡。在這種資本邏輯的強烈支配下,必然會出現對自由市場近乎信仰般的推崇以及不計後果的“浮士德式的交易——犧牲長遠利益,獲得近期利益”。為資本利益所構建的“創造性破壞”的反價值生産機制,讓這個世界徹底淪為“朝生暮死的物世界”,所有精心編織出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都不過是為商品開辟銷路的詭計。在這樣的消費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不可避免地異化為物與物的關系,以至于人的價值要由其所占有的物質财富來确證。因此,無論是吃野味、穿皮草還是别的什麼奢侈消費,其實都隻是個人身份和地位的彰顯,這其中的意義遠大于物質本身。這就是為什麼人類雖然已經意識到生态危機的來臨并為之抗争,但就整個世界範圍而言,人類在這數十年的發展中所造成的生态問題卻有增無減,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困境仍是擺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
因此,想要從根源上解決生态問題,僅靠頒布一些新法令,關閉一些污染源是不夠的,所謂的烏托邦式的道德救贖注定隻是環境保護者們的一廂情願。因為歸根結底,由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及其全球化帶來的現代生态問題的解決,植根于更深層次的人類社會的根本變革,它包括對社會制度、生産方式和民衆意識等多方面的變革。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告誡我們,當前的人類世界,無論是經濟發展理念,還是生态觀念、生活方式都存在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單憑發展自然科學與技術是不夠的,僅僅停留在社會學的現象描述上也是不充分的,隻有進入哲學層面,建構起一種蘊含生态要素的認識世界的新範式才能使之成為可能。正如《增長的極限》的作者之一喬根·蘭德所說:“一個範式就是一種世界觀。”這就提出了“哲學走向荒野”的時代任務。
(作者:伟德bevictor中文版教授、博士生導師何畏 編輯:萬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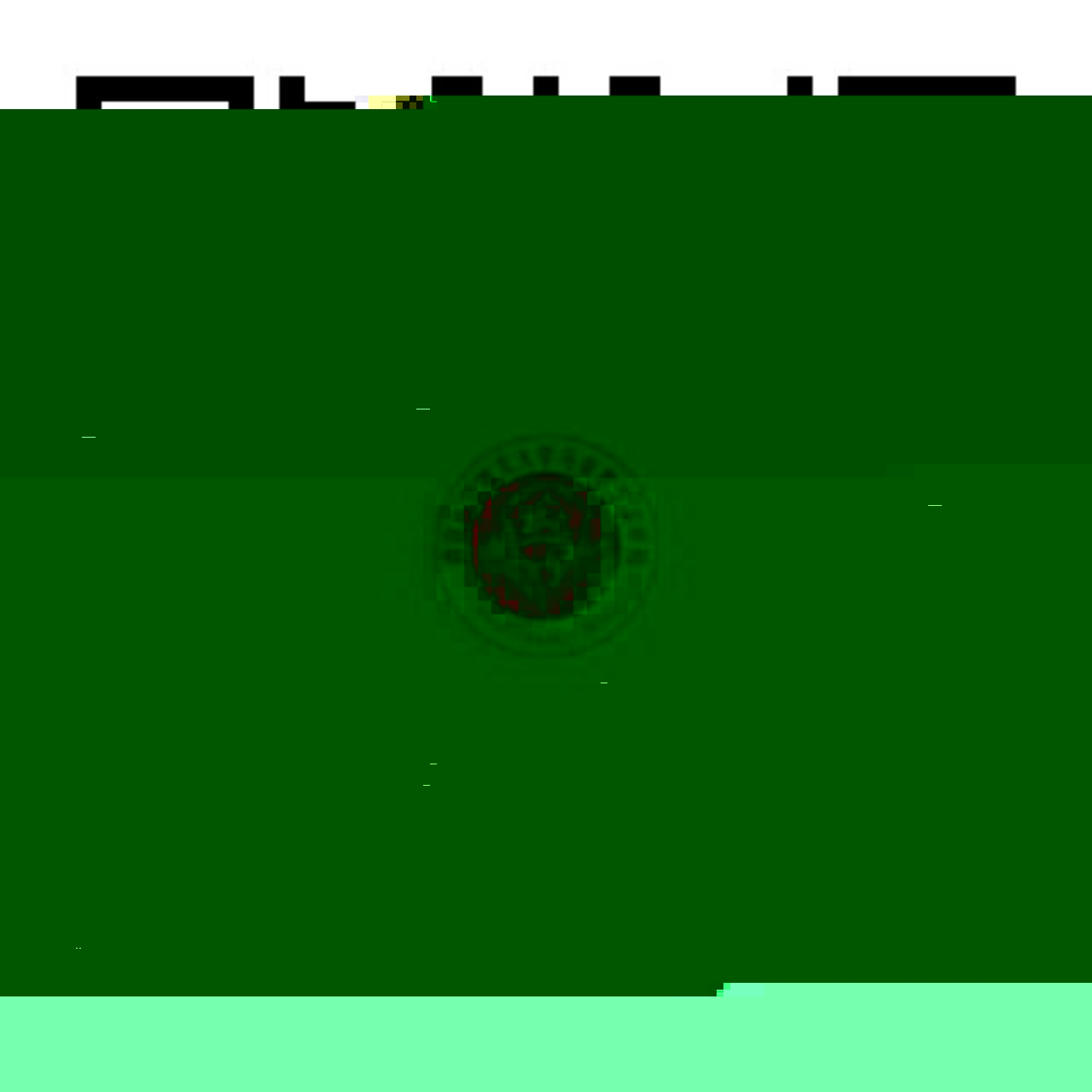
歡迎關注官方微信